《唐宋詞選釋(最新修訂本)》由國學(xué)大師俞平伯先生選注����,選錄唐宋詞二百五十一首�����,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為唐��、五代詞����,共八十七首。中��、下卷為宋詞��,共一百六十四首��。中卷題為“宋詞之一”,下卷題為“宋詞之二”��,即相當(dāng)于北宋和南宋?���!短扑卧~選釋(最新
《唐宋詞選釋(最新修訂本)》由國學(xué)大師俞平伯先生選注,選錄唐宋詞二百五十一首��,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為唐、五代詞,共八十七首。中��、下卷為宋詞�,共一百六十四首。中卷題為“宋詞之一”,下卷題為“宋詞之二”����,即相當(dāng)于北宋和南宋。《唐宋詞選釋(最新修訂本)》選詞面廣,力求體現(xiàn)詞家之風(fēng)格與詞之發(fā)展。注釋精當(dāng)權(quán)威,尤其重視對詞作真義的揭示和用語源...這個選本是提供古典文學(xué)研究工作者作為參考用的�,因此,這里想略談我對于詞的發(fā)展的看法和唐宋詞中一些具體的情況,即作為這個選本的說明�。
有兩個論點,過去在詞壇上廣泛地流傳著,雖也反映了若干實際,卻含有錯誤的成分在內(nèi):一�、詞為詩馀,比詩要狹小一些。二�、所謂“正”“變”——以某某為正�����,以某某為變�。這里只簡單地把它提出來����,在后文將要講到����。
首先應(yīng)當(dāng)說:詞的可能的����、應(yīng)有的發(fā)展和歷史上已然存在的情況�����,本是兩回事��。一般的文學(xué)史自然只能就已有的成績來做結(jié)論�,不能多牽扯到它可能怎樣,應(yīng)當(dāng)怎么樣���。但這實在是個具有基本性質(zhì)的問題���,我們今天需要討論的。《唐宋詞選釋》是一本中國古典詩詞方面有一定特色的注釋本�,喜歡詩詞的讀者不可錯過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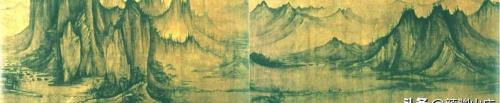
目錄:
第1章 前 言(1)
第2章 前 言(2)
第3章 附記
第4章 上卷 唐五代詞(1)
第5章 上卷 唐五代詞(2)
第6章 上卷 唐五代詞(3)
第7章 上卷 唐五代詞(4)
第8章 中卷 宋詞之一(1)
第9章 中卷 宋詞之一(2)
第10章 中卷 宋詞之一(3)
第11章 中卷 宋詞之一(4)
第12章 中卷 宋詞之一(5)
第13章 中卷 宋詞之一(6)
第14章 中卷 宋詞之一(7)
第15章 下卷 宋詞之二(1)
第16章 下卷 宋詞之二(2)
第17章 下卷 宋詞之二(3)
第18章 下卷 宋詞之二(4)
第19章 下卷 宋詞之二(5)
第20章 下卷 宋詞之二(6)
第21章 下卷 宋詞之二(7)
第22章 下卷 宋詞之二(8)
第23章 下卷 宋詞之二(9)
第24章 下卷 宋詞之二(10)
第1章 前 言(1)
這個選本是提供給古典文學(xué)研究工作者作為參考用的(亦適于廣大古典文學(xué)愛好者)����,因此�,這里想略談我對于詞的發(fā)展的看法和唐宋詞中一些具體的情況���,即作為這個選本的說明。
過去在詞壇上有兩個論點廣泛地流傳著���,它們雖也反映了若干實際,卻含有錯誤的成分在內(nèi):一�、詞為詩余����,比詩要狹小一些��。二、所謂“正”“變”——以某某為正,以某某為變�����。這里只簡單地把它提出來���,在后文將要講到���。
首先應(yīng)當(dāng)說:詞的可能的���、應(yīng)有的發(fā)展和歷史上已然存在的情況���,本是兩回事��。一般的文學(xué)史自然只能就已有的成績來作結(jié)論��,不能多牽扯到它可能怎樣�����,應(yīng)當(dāng)怎么樣��。但這實在是個具有基本性質(zhì)的問題����,是我們今天需要討論的����。以下分為三個部分來說明�。
詞以樂府代興���,在當(dāng)時應(yīng)有“新詩”的資格
詞是近古(中唐以后)的樂章����,雖已“六義附庸�����,蔚成大國”了��,實際上還是詩國中的一個小邦�����。它的確已發(fā)展了��,且到了相當(dāng)高的地位���,但按其本質(zhì)來講����,并不曾得到它應(yīng)有的發(fā)展���,并不夠大���。如以好而論��,它當(dāng)然很好了���,但也未必夠好���?���;仡櫼酝?���,大致如此��。
從詩的體裁看,歷史上原有“齊言”“雜言”的區(qū)別���,且這兩體一直在斗爭著����。中唐以前,無論詩或樂府��,“齊言”一直占著優(yōu)勢,不妨簡單地回溯一下。三百篇雖說有一言至九言的句法���,實際上多是四言����。楚辭是雜言����,但自《離騷》以降,句度亦相當(dāng)?shù)卣R。漢郊祀樂章為三言,即從楚辭變化,漢初樂府本是楚聲。漢魏以來���,民間的樂府�����,雜言頗盛�����,大體上也還是五言。那時的五言詩自更不用說了����。六朝迄隋�����,七言代興��,至少與五言有分庭抗禮的趨勢�����。到了初、盛唐���,“詩”與“樂”已成為五��、七言的天下了�����。一言以蔽之,四言→五言→七言��,是先秦至唐���,中國詩型變化的主要方向;雜言也在發(fā)展���,卻不曾得到主要的位置����。
像這樣熟悉的事情���,自無須多說�。假如這和事實不差什么�,那么���,詞的勃興,即從最表面的形式來看��,也是一樁有意義的事情;因為形式和內(nèi)容是互相影響著的。詞亦有齊言,卻以雜言為主�����,故一名“長短句”。它打破了歷代詩與樂的傳統(tǒng)形式�����,從整齊的句法中解放出來���,從此五、七言不能“獨霸”了����。這變革絕非偶然���,大約有三種因由����。
第一,隨著語言的發(fā)展而不得不變����。即以詩的正格“齊言”而論,從上列的式子看�����,由四而五而七�����,已逐漸地延長����;這明顯地為了適應(yīng)語言(包括詞匯)的變化,而不得不如此�。詩的長度,似乎七言便到了一個極限���。如八言便容易分為四言兩句���;九言則分為“四���、五”,或“五��、四”,“四�����、五”逗句更普遍一些��。但這樣的長度,在一般用文言的情況下��,雖差不多了��,如多用近代口語當(dāng)然不夠����,即摻雜用之�,恐怕也還是不夠的。長短句的特點�����,不僅參差�;以長度而論,也沖破了七言的限制����,有了很自然的八、九、十言及以上的句子。這個延長的傾向當(dāng)然并沒有停止�,到了元曲便有像《西廂記·秋暮離懷·叨叨令》那樣十七字的有名長句了����。
第二�����,隨著音樂的發(fā)展而不得不變。長短參差的句法本不限于詞,古代的雜言亦是長短句�;但詞中的長短句��,它的本性是樂句�����,是配合旋律的,并非任意從心的自由詩。這就和詩中的雜言有些不同���。當(dāng)然����,樂府古已有之,從發(fā)展來看,至少有下列兩種情形:一、音樂本身漸趨復(fù)雜�;古代樂簡����,近世樂繁。二��、將“辭”(文辭)來配聲(工譜)也有疏密的不同:古代較疏,近世較密���。這里不能詳敘了���。鄭振鐸先生說:
詞和詩并不是子母的關(guān)系����。詞是唐代可歌的新聲的總稱。這新聲中,也有可以五七言詩體來歌唱的���;但五七言的固定的句法���,萬難控御一切的新聲�����,故嶄新的長短句便不得不應(yīng)運而生��。長短句的產(chǎn)生是自然的進展,是追逐于新聲之后的必然的現(xiàn)象③����。
他在下面并引了清成肇麐《唐五代詞選自序》中的話。我想這些都符合事實,不再申說了�����。
第三,就詩體本身來說����,是否也有“窮則變”的情形呢�?當(dāng)然,唐詩以后還有宋、元�����、明��、清以至近代的詩��,決不能說“詩道窮矣”——但詩歌到了唐代��,卻有極盛難繼之勢����。如陸游說:
唐自大中后����,詩家日趣(通“趨”)淺薄�,其間杰出者亦不復(fù)有前輩宏妙渾厚之作����,久而自厭�,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tài)���,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故歷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輒簡古可愛。蓋天寶以后詩人常恨文不迨(似缺一“意”字)�����,大中以后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所長格力��,施于所短��,則后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一����,能此而不能彼����,未能以理推也①��。
他雖說“未能以理推”��,實際上對于形式與內(nèi)容的關(guān)系和推陳出新的重要也已經(jīng)約略看到了�����。詞的初起�����,確有一種明朗清爽的氣息�����,為詩國別開生面����。陸游的話只就《花間集》一集說,還不夠全面���,然亦可見一斑�����。
這樣說來�,詞的興起��,自非偶然,而且就它的發(fā)展可能性來看���,可以有更廣闊的前途,還應(yīng)當(dāng)有比它事實上的發(fā)展更加深長的意義�����。它不僅是“新聲”�,而且應(yīng)當(dāng)是“新詩”���。唐代一些詩文大家已有變古創(chuàng)新的企圖,且相當(dāng)程度地實現(xiàn)了����。詞出詩外���,源頭雖若“濫觴”�����,本亦有發(fā)展為長江大河的可能����,像詩一樣地浩瀚�,而自《花間集》以后�,大都類似清溪曲澗,雖未嘗沒有曲折幽雅的小景動人流連,而壯闊的波濤終為不足。在文學(xué)史上���,詞便成為詩之余,不管為五、七言之余也罷�����,三百篇之余也罷,反正只是“余”。但它為什么是“余”呢�����?并沒有什么理由可言。這一點,前人早已說過,我卻認為他們估計得似乎還不大夠。以下從詞體的特點來談它應(yīng)有的和已有的發(fā)展���。
詞的發(fā)展的方向
要談詞的發(fā)展���,首先當(dāng)明詞體的特點、優(yōu)點����,再看看是否已經(jīng)發(fā)揮得足夠了�����。
當(dāng)然�����,以詩的傳統(tǒng)而論�,齊言體如四�、五��、七言盡有它的優(yōu)點��;從解放的角度來看“詩”,詞之后有曲�����,曲也有更多的優(yōu)點。在這里只就詞言詞�。就個人想到的�,以下列舉五條�,恐怕還不完全�。
一是各式各樣的�,多變化的����。假如把五、七言比作方或圓,那么詞便是多角形;假如把五�、七言比作直線,詞便是曲線。它的格式:據(jù)萬樹《詞律》�����,為調(diào)六百六十,為體一千一百八十余;清康熙《欽定詞譜》��,調(diào)八百二十六,體二千三百零六�����。如說它有兩千個格式����,距事實大致不遠。這或者是后來發(fā)展的結(jié)果,詞初起時�,未必有那么多����,也不會太少����,如《宋史·樂志》稱“其急慢諸曲幾千數(shù)”����。不過《樂志》所稱���,自指曲譜說,未必都有文辭罷了�。
二是有彈性的�。據(jù)上列數(shù)目字��,“體”之于“調(diào)”��,約為三比一�。詞譜上每列著許多的“又一體”�,使人目眩。三比一者����,平均之?dāng)?shù);以個別論,也有更多的����,如柳永《樂章集》所錄《傾杯》一調(diào)即有七體之多����。這些“又一體”,按其實際�����,或由字數(shù)的多少��,或緣句逗的參差,也有用襯字的關(guān)系�。詞中襯字����,情形本與后來之曲相同����。早年如敦煌發(fā)現(xiàn)的“曲子詞”就要多些�����,后來也未嘗沒有。以本書所錄,如滄海之一粟,也可以看到①。不過一般不注襯字,因詞譜上照例不分正襯����。如分正襯���,自然不會有那么多的“又一體”了����。是否變化少了呢?不然。那應(yīng)當(dāng)更多���。這看金�����、元以來的曲子就可以明白�。換句話說,詞的彈性很大,實在可以超過譜上所載兩千多個格式的����,只是早年的作者們已比較拘謹�����,后來因詞調(diào)失傳,后輩作者就更加拘謹了�����。好像填詞與作曲應(yīng)當(dāng)各自一工����。其實按詞曲為樂府的本質(zhì)來說,并看不出有這么劃然區(qū)分的必要�。詞也盡可以奔放馳驟的啊�����。
三是有韻律的。這兩千多格式����,雖表面上令人頭暈眼花��,卻不是毫無理由而存在的����。它大多數(shù)從配合音樂旋律來的����。后人有些“自度腔”��,或者不解音樂�,出于杜撰����,卻是極少數(shù)。早年“自度腔”每配合音譜,如姜白石的詞�。因此好的詞牌�,本身含著一種情感�����,所謂“調(diào)情”���。盡管旋律節(jié)奏上的和諧與吟誦的和諧并不就是一回事,也有仿佛不利于唇吻的���,呼為“拗體”�,但有些拗體�,假如仔細吟味��,拗折之中亦自饒和婉。這須分別觀之。所以這歌與誦的兩種和諧,雖其間有些距離,也不完全是兩回事——話雖如此���,自來談?wù)撨@方面的�,以我所知�����,似都為片段��,東鱗西爪,積極地發(fā)揮的少�����,系統(tǒng)地研究的更少。我們并不曾充分掌握��、分析過這兩千多個詞調(diào)啊����。
四它在最初���,是接近口語的��。它用口語��,亦用文言�����;有文言多一些的�,有白話多一些的�����,也有二者并用的。語文參錯得相當(dāng)調(diào)和���,形式也比較適當(dāng)。這個傳統(tǒng),在后來的詞里一直保持著��。五、七言體所不能����,或不易表達的,在詞則多半能夠委曲詳盡地表達出來����。它所以相當(dāng)?shù)嘏d旺,為人們所喜愛����,這也是緣由之一��。
五它在最初,是相當(dāng)?shù)胤从超F(xiàn)實的�����。它是樂歌�、徒歌(民歌)��,又是詩,作者不限于某一階層�,大都是接近民間的知識分子寫的��。題材又較廣泛��。有些作品���,藝術(shù)的意味、價值或者要差一些,但就傳達人民的情感這一角度來看,方向本是對的���。
看上面列舉的不能不算做詞的優(yōu)點,經(jīng)歷了漫長的時間���,詞在數(shù)量上或質(zhì)量上已大大地發(fā)展了。但它們是否已將這些特長發(fā)揮盡致了呢?恐怕還沒有�����。要談這問題�,先當(dāng)約略地探討一般發(fā)展的徑路,然后再回到個別方面去。
一切事物的發(fā)展,本應(yīng)當(dāng)后起轉(zhuǎn)精�����,或后來居上的,所謂“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毫無疑問���,文藝應(yīng)當(dāng)向著深處前進�,這是它的主要方向;卻不僅僅如此,另一方面是廣?!吧睢辈槐厣願W���,而是思想性或藝術(shù)性高��?�!皬V”不必數(shù)量多���,而是反映面大�����。如從來論詩���,有大家�、名家之別���。所謂“大家”者,廣而且深;所謂“名家”者����,深而欠廣。一個好比盤結(jié)千里的大山���,一個好比峭拔千尋的奇峰���。在人們的感覺上��,或者奇峰更高一些;若依海平實測,則大山的主峰,其高度每遠出奇峰之上,以突起而見高,不過是我們主觀上的錯覺罷了�。且不但大家�、名家有這樣的分別,即同是大家��,也有深廣的不同�����。如杜甫的詩深而且廣��,李白的詩高妙不弱于杜��,或仿佛過之���,若以反映面的廣狹而論����,那就不能相提并論了。
詞的發(fā)展本有兩條路線:一����、廣而且深(廣深),二、深而不廣(狹深)�。在當(dāng)時的封建社會里,受著歷史的局限�,很不容易走廣而且深的道路,它在文士們手中便轉(zhuǎn)入狹深這一條路上去;因此就最早的詞的文學(xué)總集《花間集》來看����,即已開始走著狹深的道路。歐陽炯《花間集序》上說:
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fēng)�����,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fēng)�����,寧尋越艷;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庶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
“曲子詞”為詞的初名����?!扒闭?,聲音��;“詞”者�����,文辭(辭);稱“曲子”者��,“子”有“小”字義�����,蓋以別于大曲。這里在原有的“曲子詞”上面加上“詩客”二字��,成為“詩客曲子詞”����,如翻成白話�,便是詩人們作的“曲子詞”,以別于民間的歌唱����,這是非常明白的�����。歐陽炯序里提出“南朝宮體”“北里倡風(fēng)”的概括和“言之不文”“秀而不實”的批評�����,像這樣有對立意味又不必合于事實的看法����,可以說����,詞在最初已走著一條狹路�����,此后歷南唐兩宋未嘗沒有豪杰之士自制新篇�����,其風(fēng)格題材每逸出《花間集》的范圍����;但其為“詩客曲子詞”的性質(zhì)卻沒有改變�����,亦不能發(fā)生有意識的變革��。“花間”的潛勢力依然籠罩了詞壇千年��。
我們試從個別方面談���,首先當(dāng)提出敦煌曲子。敦煌寫本�,最晚到北宋初年�����,卻無至道��、咸平以后的���;這些曲子自皆為唐五代的作品���。舊傳唐五代詞約有一千一百四十八首(見近人林大椿輯本《唐五代詞》)�,今又增加了一百六十二首����。不但數(shù)量增多了�,而且反映面也增廣,如唐末農(nóng)民起義等�,這些在《花間集》里就蹤影毫無����。以作者而論��,不限于文人詩客���,則有“邊客游子之呻吟,忠臣義士之壯語,隱君子之怡情悅志�,少年學(xué)子之熱望與失望”。以調(diào)子而論����,令��、引����、近��、慢已完全了�,如《鳳歸云》�、《傾杯》、《內(nèi)家嬌》都是長調(diào),則慢詞的興起遠在北宋以前�����。以題材而論,情形已如上述,“其言閨情與花柳者��,尚不及半”(亦根據(jù)王說)�,可破《花間集序》宮體、倡風(fēng)之妄說����。過去的看法是�����,詞初起時��,其體為小令,其詞為艷曲��。就《花間集》說來誠然如此����,但《花間集》已非詞的最初面目了��,因此這樣的說法是片面的。
第2章 前 言(2)
以文章來論,有很差的,也有很好的。有些不下于《花間集》溫、韋諸人之作��,因其中亦雜有文人的作品�。有的另具一種清新活潑的氣息��,為民歌所獨有���,如本書上卷第一部分所錄���,亦可見一斑。它的支流到宋代仍綿綿不斷����,表現(xiàn)在下列兩個方面:一、民間仍然作著“曲子詞”���。這些材料,可惜保存得很少,散見各書��,《全宋詞》最末數(shù)卷(二九八至三○○卷)���,輯錄若干首,如雖寫情戀,當(dāng)時傳為暗示北宋末年動亂的�,如寫南宋里巷風(fēng)俗的……反映面依然相當(dāng)廣泛�����。若說“花間”派盛行之后���,敦煌曲子一派即風(fēng)流頓盡了�,這也未必盡然����。二���、所謂“名家”每另有一種白話詞��,兼收在集子里����,如秦觀的《淮海居士長短句》��、周邦彥的《清真詞》都有少數(shù)純粹口語體的詞�,我們讀起來卻比“正規(guī)”的詞還要難懂些�?�?梢娝未坏话闵鐣巷L(fēng)尚如此�,即專門名家亦會偶一用之���。至于詞篇����,于藻飾中雜用白話��,一向如此,迄今未變�����,又不在話下了����。陳郁《藏一話腴》評周詞說:“美成自號清真����,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貴人學(xué)士、市儇伎女皆知美成詞為可愛。”是雅俗并重��,仍為詞的傳統(tǒng)���,直到南宋���,未嘗廢棄�����。
如上所說�����,“花間”諸詞家走著狹深的道路�,對民間的詞不很贊成;實際上他們也依然部分繼承著這個傳統(tǒng),不過將原來的艷體部分特別加大、加工而已����。一般說來���,這些詞思想性差,反映面狹�。但其中也有表現(xiàn)民俗的���,如歐陽炯、李珣的《南鄉(xiāng)子》���;也有個別感懷身世的����,如鹿虔的《臨江仙》,并非百分之百的艷體。至于藝術(shù)性較高�����,前人有推崇過當(dāng)處,卻也不可一概抹殺�。
此后的發(fā)展也包括兩個方面,舉重點來說:其一承著這傳統(tǒng)向前進展�����,在北宋為柳永�、秦觀�、周邦彥,在南宋為史達祖�����、吳文英���、王沂孫等�;其二不受這傳統(tǒng)的拘束,有如李煜����、蘇軾、辛棄疾等�����。這不過是大概的看法����,有些作家不易歸入哪一方面的,如李清照、姜夔。這里擬改變過去一般評述的方式,先從第二方面談起��。
“南唐”之變“花間”�,變其作風(fēng)不變其體——仍為令����、引之類���。如王國維關(guān)于馮延巳�、李后主詞的評述���,或不符史實����,或估價奇高;但他認為南唐詞在“花間”范圍之外�,堂廡特大��,李后主的詞�,溫、韋無此氣象�,這些說法還是對的。南唐詞確推擴了“花間”的面貌,而開北宋一代的風(fēng)氣�。
蘇東坡創(chuàng)作新詞����,無論題材、風(fēng)格都有大大的發(fā)展��,而后來論者對他每有微辭����,宋人即已如此�����。同時如晁補之說:“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辭橫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稍晚如李清照說:“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xué)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xié)音律者���,何耶?”③若依我看來,東坡的寫法本是詞發(fā)展的正軌��,他們認為變格����、變調(diào)�,實系顛倒���。晁����、李都說他不合律,這也是個問題��。如不合律,則縱佳����,亦非曲子�,話雖不錯���,但何謂合律�����,卻是一個復(fù)雜的問題���。東坡的詞,既非盡不可歌;他人的詞也未必盡可歌,可歌也未必盡合律,均屢見于記載。如周邦彥以“知音”獨步兩宋,而張炎仍說他有未諧音律處①,可見此事,專家意見紛歧��,不適于作文藝批評的準則���。至于后世����,詞調(diào)亡逸,則其合律與否都無實際意義,即使有,也很少了,而論者猶龂龂于去上陰陽之辨�,誠無謂也����。因此東坡的詞在當(dāng)日或者還有些問題���,在今日就不成為問題了����。胡寅說:“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tài)��,擺脫綢繆宛轉(zhuǎn)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于是《花間》為皂隸��,而柳氏為輿臺矣�?!边@是詞的一大進展����。
李清照在《論詞》里����,主張協(xié)律;又歷評北宋諸家均有所不滿�,而曰“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似乎夸大?�,F(xiàn)在我們看她的詞卻能夠相當(dāng)?shù)貙嵭凶约旱睦碚摚⒎强照勂凼?����。她擅長白描��,善用口語,不艱深�,也不庸俗���,真所謂“別是一家”����?���?上淮?,現(xiàn)有的只零星篇什而已�����。至于她在南渡以后雖多傷亂憂生之詞,反映面仍尚覺未廣���,這是身世所限����,亦不足為病。
南宋的詞,自以辛棄疾為巨擘�����。向來蘇辛并稱��,但蘇、辛并非完全一路�����。東坡的詞如行云流水�,若不經(jīng)意����,而氣體高妙�����,在本集大體勻稱。稼軒的詞亂跑野馬����,非無法度���,奔放馳驟的極其奔放馳驟��,細膩熨帖的又極其細膩熨帖���,表面上似乎不一致���。周濟說他“斂雄心,抗高調(diào)���,變溫婉����,成悲涼��。”其所以慷慨悲歌��,正因壯心未已���,而本質(zhì)上仍是溫婉,只變其面目使人不覺罷了。照這樣說來���,他骨子里還是一貫的���。稼軒詞篇什很廣���,技巧很繁雜,南宋詞人追隨他的也很多。在詞的發(fā)展方面��,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作家��。
姜夔的詞在南宋負高名,卻難得位置�,評論也難得中肯�。如宋末的張炎應(yīng)該算是知道白石的了���,他在《詞源》里,說白石詞“清空”����、“清虛”��、“騷雅”����、“如野云孤飛,去留無跡”等���,似乎被他說著了�,又似乎不曾���,很讓人覺得渺茫��。白石與從前詞家的關(guān)系�,過去評家的說法也不一致�����,有說他可比清真的���,有說他脫胎稼軒的���。其實為什么不許他自成一家呢���?他有襲舊處,也有創(chuàng)新處,而主要的成績應(yīng)當(dāng)在創(chuàng)新方面。沈義父《樂府指迷》說他“未免有生硬處”�,雖似貶詞��,所謂“生硬”已暗逗了這消息��。他的詞��,有個別反映了當(dāng)時的現(xiàn)實,只比稼軒要含蓄一些�,曲折一些��。他的創(chuàng)作理論,有變古的傾向,亦見于本集自序,說得也很精辟。
上面約略評述的幾個詞家�,都不受“花間”以來傳統(tǒng)的拘束�。他們不必有意變古�����,而事實上已在創(chuàng)新����。至于所謂正統(tǒng)派的詞家����,自“花間”以來也不斷地進展著�,并非沒有變化����,卻走著與過去相似的道路。這里只重點地略說三人,在北宋為柳永、周邦彥,在南宋為吳文英���。其他名家���,不及一一列舉了�。
柳永詞之于《花間集》,在聲調(diào)技巧方面進展很大。如《花間集》純?yōu)榱钋?,《樂章集》慢詞獨多,此李清照所謂“變舊聲作新聲”也�����。柳詞多用俗語�����,長于鋪敘�,局度開闊��,也是它的特點���。就其本質(zhì)內(nèi)容來說,卻不曾變��,仍為情態(tài)香艷之詞�����,綺靡且有甚于昔���。集中亦有“雅詞”��,只占極少數(shù)�,例如本書中卷所錄《八聲甘州》����。
周邦彥詞�����,令��、慢兼工��,聲調(diào)方面更大大地進展④�。雖后人評他的詞�����,“創(chuàng)調(diào)之才多����,創(chuàng)意之才少”����,固有道著處��,亦未必盡然��。周詞實為《花間集》之后勁��,近承秦、柳����,下啟南宋����,對后來詞家影響很大。
一般地說�,南宋名家都祖《清真》而祧《花間》��,尤以吳文英詞與周邦彥詞更為接近�����。宋代詞評家都說夢窗出于清真�,不僅反映面窄小�����,藝術(shù)方面亦有形式主義的傾向�����。如清真的綿密,夢窗轉(zhuǎn)為晦澀����;清真的繁秾,夢窗轉(zhuǎn)為堆砌���,都是變本加厲����。全集中明快的詞占極少數(shù)�����。如仔細分析,則所謂“人不可曉”者亦自有脈絡(luò)可尋����,但這樣的讀詞�����,未免使人為難了。說它為狹深的典型�����,當(dāng)不為過��。詞如按照這條路走去��,越往前走便越覺其暗淡,如清末詞人多學(xué)夢窗�����,就是不容易為一般讀者接受的�。
南宋還有很多的詞家���,比較北宋更顯得繁雜而不平衡;有極粗糙的,有很工細的,有注重形式美的��,也有連形式也不甚美的,不能一概而論。大體上反映時代的動亂�����、個人的苦悶����,都比較鮮明����,如本書下卷所錄可見一斑。不但辛棄疾��、二劉(劉過、劉克莊)如此���,姜夔如此,即吳文英�����、史達祖�����、周密�、王沂孫、張炎亦未嘗不如此��。有些詞人情緒之低沉�����,思想之頹墮�����,缺點自無可諱言;他們卻每通過典故辭藻的掩飾���,曲折地傳達眷懷家國的感情����,這不能不說比之“花間”詞為深刻�����,也比北宋詞有較大的進展�����。
以上都是我個人的看法�,拉雜草率��,未必正確���。所述各家�����,只舉出若干“點”��,不能代表“面”,或者隱約地可以看到連絡(luò)的“線”來:這“線”就表示出詞的發(fā)展的兩個方向。這非創(chuàng)見,過去詞論家�����、評家、選家都看到了這樣的事實�����。他們卻有“正變”之說�����。顯明的事例���,如周濟《詞辨》之分為上、下兩卷,以溫、韋等為正��,蘇���、辛等為變����。這樣一來,非但說不出正當(dāng)?shù)睦碛?����,事實上恰好顛倒了。他們所謂“正”,是以《花間集》為標準而言,其實《花間集》遠遠不夠“正”。如陸游說:
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嘆也哉��!或者出于無聊故耶����。
《花間集》如何可作為詞的標準呢��!《花間集》既不足為準,則正變云云即屬無根�。我們不必將正變倒過來用�,卻盡可以說,蘇、辛一路,本為詞的康莊大道��,而非磽確小徑�����。說他們不夠倒是有的���;說他們不對卻不然�。如陳無己說:
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要非本色”����,即使“極天下之工”也還是不成,這樣的說法已很勉強����;何況所謂“本色”無非指“花間”��、柳七之類����,非真正的本色。本色蓋非他,即詞的本來面目,如今傳唐人“曲子”近之����。它的反映面廣闊,豈不能包后來蘇�����、辛諸詞在內(nèi)����?因此���,過去的變化�,其病不在于逸出范圍,相反地,在于還不夠廣闊�。
詞的本色是健康的���,它的發(fā)展應(yīng)當(dāng)更大���,成就應(yīng)當(dāng)更高�。其所以受到限制��,首先關(guān)鍵在于思想;其次,形式方面也未能充分利用�。以歷史的觀點�,我們自然不能多責(zé)備前人��。過去的各種詩型,這里所說“曲子詞”以外��,尚有散曲�����、民歌等,都有成為廣義新詩中一體的希望。
關(guān)于選釋本的一些說明
《唐宋詞選釋》自唐迄南宋,共二百五十一首,分為三卷�����。上卷為唐、五代詞��,又分為三部分:一����、唐���,二、《花間集》�,三��、南唐����,共八十七首��。中����、下卷為宋詞����,共一百六十四首。中卷題為“宋詞之一”�,下卷題為“宋詞之二”�,即相當(dāng)于北宋和南宋�����。其所以不曰北��、南����,而分一��、二者����,因南渡詞人正當(dāng)兩宋之際��,其屬前屬后每每兩可���,不易恰當(dāng)。其反映時代動蕩的作品大部分錄在下卷。中、下兩卷之區(qū)別���,也想約略表示出兩宋詞的面貌�����,有少數(shù)作家不專以其年代先后來分�����。如葉夢得生年較早,今所錄二首均南渡以后之作,故移下卷。張孝祥生年稍晚�����,所錄《六州歌頭》作于1163年���,《念奴嬌》作于1166年,時代均較早,且反映南宋初年政治情況���,故置韓元吉諸人之前。
因本書主要為提供古典文學(xué)研究者參考之用�����,做法與一般普及性的選本有所不同,選詞的面稍寬,想努力體現(xiàn)出詞家的風(fēng)格特色和詞的發(fā)展途徑���。但唐宋詞翰,浩如煙海��,今所選二百五十余篇��,只是一勺水罷了�����,真古人所謂“以蠡測?�!?��。詞的發(fā)展途徑(如上文所說)��,本書是否體現(xiàn)出來了呢���?恐怕沒有�。即以某一詞家論��,所選亦未必能代表他的全貌。例如中卷柳永詞���,取其較雅者��,看不出他俚俗浮艷的特點;下卷吳文英詞��,取其較明快者�,看不出他堆砌晦澀的特點。這也是一般選本的情況�,本書亦非例外��。
下文借本書說明一些注釋的情況�����。
作“注”原比較復(fù)雜��。有些是必須作注的。以本文為例,如姜夔的《疏影》:“那人正睡里��,飛近蛾綠。”設(shè)若不注“那人”是誰���,誰在睡覺�����?又如辛棄疾的《鷓鴣天》“書咄咄”句用晉殷浩事,一般大都這樣注����;但殷浩“咄咄書空”表示他熱中名利�����,和辛的性格與本篇的詞意絕不相符�����,若不作注��,就更不妥了�。有些似乎可注可不注���,如引用前人之句說明本句或本篇�。這個是否必要呢����?依我看�����,也有些必要,我不避孤陋之誚�����,在這選本中妄下了若干條注。雖然分量似已不少�,離完備還差得多。
前人寫作以有出典為貴,評家亦以“無一字無來歷”為高?�;ハ嘁蛞u�����,相習(xí)成風(fēng)��,過去有這樣的情形�����,其是非暫置不論�。其另一種情形:雖時代相先后���,卻并無因襲的關(guān)系�����。有些情感,有些想象,不必誰抄襲誰�����。例如李后主《浪淘沙》中的名句“別時容易見時難”����,前人說它出于《顏氏家訓(xùn)》的“別易會難”,引見上卷李煜此篇注③��。果真是這樣嗎?恐怕未必���。所以二者相似����,或竟相同,未必就有關(guān)聯(lián)�,也未必竟無關(guān)聯(lián)�����,究竟誰是偶合��,誰是承用,得看具體的情況來決定��。所謂“看”�,當(dāng)然用注家的眼光看����,那就不免有他的主觀成分在內(nèi)了�����。
而且所謂“二者”�����,本不止二者����,要多得多���,這就更加復(fù)雜了���。譬如以本句為甲���,比它早一點的句子為乙����,卻還有比乙更早的丙丁戊己呢�。蓋杜甫詩所謂“遞相祖述復(fù)先誰”也。注家引用的文句���,大都不過聊供參考而已。若云某出于某,卻是不敢這樣保證的。
再說�����,可以增進了解,這情形也很復(fù)雜���。如以乙句注甲句,而兩句差不多����;讀者如不懂得甲���,正未必懂得乙�。其另一種情形���,注文甚至于比本文還要深些,那就更不合理了��。怎么會發(fā)生這類情形的呢?因為作注�,照例以前注后,更著重最早的出典,故注中所引材料每較本文為古�����,如《詩》��、《書》���、《史》����、《漢》之類��,總要比唐詩����、宋詞更難懂一些��,這就常常造成這似乎顛倒的情況。然所注縱有時難懂,卻不能因噎廢食。注還是可以相當(dāng)增進了解、擴大眼光的。將“注”和“釋”分開來看�����,只為了說明的方便�����,其實“注”也是釋���,而且是比較客觀的“釋”。古典浩瀚,情形繁復(fù)���,有詩文的差別�����,有古今言語的隔閡。有些較容易直接解釋,有些只能引用許多事例作為比較����,使讀者自會其意�����。如近人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其中每一條開首為解釋�����,下面所附為原材料�����。其功力最深、用途最大的即在他所引許多實例��,至于他的解釋雖然大致不差,也未必完全可靠。我們將這些實例����,比較歸納起來��,就可以得出與張氏相同的結(jié)論���,也可以得出和他不盡相同的結(jié)論�����,會比他更進一步。這樣,我認為正得張氏作書之意。書名“匯釋”,“匯”才能“釋”�,與其不“匯”而“釋”,似無寧“匯”而不“釋”。因若觸類旁通,你自然會得到解釋的��。
以上所談�����,是為了使讀者明了注釋一般的情況以及如何利用它��,原非為本書的缺點解嘲����。就本書來說,誠恐不免尚有錯誤。當(dāng)選錄和注釋之初�,原想盡力排除個人主觀的偏愛成見�,而忠實地將古人的作品�����、作意介紹給讀者�;及寫完一看����,這個選本雖稍有新意�,仍未脫前人的窠臼�����。選材方面����,或偏于消極傷感�����,或過于香艷纖巧�,這雖然和詞本身發(fā)展的缺陷有關(guān),但以今日觀之����,總不恰當(dāng)�����。而且注釋中關(guān)于作意的分析和時代背景的論述��,上���、中兩卷亦較下卷為少���。注釋的其他毛病�,如深而不淺�����,曲而未達���,偏而不全,掉書袋又不利落,文言��、白話相夾雜等,那就更多了。自己也難得滿意�����,更切盼讀者指教。
第3章 附記
前編《唐宋詞選》有試印本,至今已十六年。近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同志來�����,說要正式出版����,文學(xué)研究所也表示贊同�����。起初我還很躊躇;為了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響應(yīng)黨的號召,經(jīng)過思考,也就同意了�����。但舊本的缺點需要修整�,我勉力從事�����,做得很慢。
現(xiàn)改名《唐宋詞選釋》��,除刪去存疑的兩首�����,余未動�,雖經(jīng)修訂����,仍未必完善�。如內(nèi)容形式過于陳舊�,解說文白雜用���,繁簡不均,深入未能淺出等�����;且或不免有其他的錯誤,請讀者指正���。
編寫之中,承友人與出版社同志殷勤相助,深表感謝。
第4章 上卷 唐五代詞(1)
虞美人
李 煜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fēng)�����,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yīng)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敦煌曲子詞
菩薩蠻①
枕前發(fā)盡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爛�。水面上秤錘浮,直待黃河徹底枯�����。白日參辰現(xiàn)②�����,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見日頭③�����。
【注釋】
①這篇疊用許多人世斷不可能的事作為比喻����,和漢樂府《上邪》相似�。但那詩山盟海誓是直說;這里反說����,雖發(fā)盡千般愿���,畢竟負了心,卻是不曾說破。②“參”“辰”���,兩星名。參(shēn)����,參宿���,在西方�����;辰�,心宿,在東方。天體上距離約一百八十度。出沒不相值,亦叫“參”、“商”���。辰為商(殷商)星��,見《左傳·昭公元年》。參�����、辰本不能并見�����,況在白晝����。③縱然具備上邊所說各項條件,盟誓可以罷休�,卻仍不能休����,還要等待三更時看見日頭����。一意分作兩層,加重之辭��。
浣溪沙
五里竿頭風(fēng)欲平①�����。長風(fēng)舉棹覺船行����。柔櫓不施停卻棹�,是船行②�。滿眼風(fēng)波多灼,看山恰似走來迎。子細看山山不動�����,是船行③����。
【注釋】
①“竿頭”或校作“灘頭”?���!拔謇铩币蔀椤拔鍍伞敝`���。五兩����,雞毛制�����,占風(fēng)具。郭璞《江賦》:“覘五兩之動靜��?��!比绮桓淖?����,解釋為船行五里,風(fēng)忽小了���,亦通�����。②“長風(fēng)”似與上文“風(fēng)欲平”矛盾�����,故或校作“張帆”。但張帆即無須舉棹�,這里恐是倒句����。追敘風(fēng)未平、未轉(zhuǎn)順風(fēng)時的狀況�����。逆風(fēng)劃船,走得很慢�,所以說“覺船行”?���!芭e棹”正和“停卻棹”對��,反起下文不搖船�,順風(fēng)掛帆�,船走快了����,所以說“是船行”。兩語相承��,用“覺”“是”兩字分點,似復(fù)非復(fù)�����。③梁元帝《早發(fā)龍巢》:“不疑行舫動����,惟看遠樹來����?��!?/p>
望江南
天上月�����,遙望似一團銀���。夜久更闌風(fēng)漸緊�����,為奴吹散月邊云,照見負心人����。
鵲踏枝①
叵耐②靈鵲③多語④��,送喜何曾有憑據(jù)�����。幾度飛來活捉取,鎖上金籠休共語⑤����。比擬⑥好心來送喜�����,誰知鎖我在金籠里。欲他征夫早歸來,騰身卻放我向青云里����。
【注釋】
①“鵲踏枝”為“蝶戀花”之異名����。這和后來的“蝶戀花”,句法亦頗不同����,故仍其原題���。②“叵”是“可”的反文�����,不可也;讀為“不可”的合音����。叵耐��,不可耐�����。猶俗語說“叵測”��,不可測����。③《淮南子·氾論訓(xùn)》高注:“乾鵠�����,鵲也�,人將有來客���,憂喜之征則鳴����?!薄堕_元天寶遺事》:“時人之家聞鵲聲皆以為喜兆����,故謂靈鵲報喜��?���!苯策€有這種迷信的說法���。參看下宋歐陽修《玉樓春》注⑤。④原作“滿語”����,“滿”字疑是“”之形誤�����,欺瞞���。或校作“謾”���。“”與“滿”較近���。⑤不要和他說話�����,即不要聽他的話�����。⑥“比擬”��,準備����。
別仙子①
此時模樣��,算來是秋天月�����。無一事,堪惆悵�����,須圓闕②����。穿窗牖��,人寂靜����,滿面蟾光如雪���。照淚痕何似,兩眉雙結(jié)��。曉樓鐘動,執(zhí)纖手���,看看③別��。移銀燭,偎身泣����,聲哽噎����。家私事�,頻付囑,上馬臨行說����。長思憶�����,莫負少年時節(jié)④��。
【注釋】
①全篇從男子方面��,追憶離別��,描寫對方。開首借月比人����,即以月的圓缺來說明人事的變遷����;以后用月影穿窗照見美人�����,實寫臨別情景�,直貫篇終����。②人本和月一樣地圓滿����,所以說無一事堪惆悵����,只是月有圓缺��,人有離合,未免可惜,即是可惆悵��。圓闕并列�����,卻重在“闕”���?���!绊殘A闕”,須有圓缺�����,定有圓缺的意思,唯口氣較軟。須猶應(yīng)也��,必也����,見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卷一。③“看看”��,轉(zhuǎn)眼�,估量時間之辭���,見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卷六�����。④這是總結(jié)上文的種種的叮嚀囑咐,語在虛實之間。
南歌子二首①
斜影珠簾立②�����,情事共誰親�?分明面上指痕新?羅帶同心③誰綰?甚人踏裰④裙���?蟬鬢因何亂�����?金釵為甚分�?紅妝垂淚憶何君��?分明殿前直說,莫沉吟�。
自從君去后�,無心戀別人�����。夢中面上指痕新⑤��。羅帶同心自綰�。被蠻兒⑥踏裰裙。蟬鬢珠簾亂⑦���,金釵舊股分⑧。紅妝垂淚哭郎君����。信是南山松柏��,無心戀別人�����。
【注釋】
①設(shè)為男女兩方相互問答���。這是民歌的一種形式���,源流都很長遠��。詞的初起,有多樣不同的風(fēng)格���。此二首有意校字。第二首“哭郎君”以下原在另一首上���,蓋是錯簡�����,今校改�。②“影”�,原作�,將“彡”搬在左邊,即影字的俗寫���。人的影子映著珠簾�����。或?qū)ⅰ坝啊备臑椤耙小?���,未是?/p>
③“同心”���,結(jié)子的一種式樣��,表示恩愛。④“裰”,補也���,文義不合���,當(dāng)是錯字����?����;蛞聘]梁賓《喜盧郎及第》:“小玉驚人踏破裙”句校作“破”?�!捌啤笨勺髡Z助用,當(dāng)輕讀���。⑤說面上的指痕是自己夢中弄上的���。
⑥“蠻”校改字�����,原作“”����,誤��?��!靶U兒”,小兒����。李賀《馬詩》:“吾聞果下馬,羈策任蠻兒�����?��!雹呒从迷谝粏枴靶庇爸楹熈ⅲ槭鹿舱l親”���,回答第五問“蟬鬢因何亂”�����,章法整中有散����。⑧金釵是早年丟掉的����,或從前別君時所分��,所以說“舊股分”���。
拋球樂
珠淚紛紛濕綺羅���,少年公子負恩多�。當(dāng)初姊姊分明道��,莫把真心過與他①�����。子細思量著�。淡薄知聞解好么②��?
【注釋】
①白描寫法�,口氣神情非常婉轉(zhuǎn),不像一般的七言詩句�,別具一種風(fēng)格���?!八?���,(tuō)�。②“知聞”在唐詩中���,或作名詞用�����,或作動詞用�����,詳見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卷五���。這里當(dāng)是名詞�����,作朋友�����、相知解。若釋為過從結(jié)交����,當(dāng)動詞用����,就和下文“解”字相犯,一句中有了兩個謂語反而費解��。“淡薄知聞”是一個詞組�����,和張書所引“琴里知聞”“酒知聞”相像�����。這句如翻成現(xiàn)代語�����,大略是:薄幸的相知懂得人好心嗎�?是承上“少年公子負恩多”�,說出這首詞的本意。
李 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生于碎葉城(當(dāng)時屬安西都護府),后遷居四川�����。天寶初���,入長安���,賀知章一見����,稱為“謫仙人”,薦于唐玄宗�,待詔翰林。后漫游江湖間,被永王李璘聘為幕僚�。璘起兵�����,事敗,白坐流放夜郎(在今貴州?。?���。中途遇赦����,至當(dāng)涂依李陽冰�,未幾卒。
李白所作詞����,宋人已有傳說(如文瑩《湘山野錄》卷上)。證以崔令欽《教坊記》及今所傳敦煌卷子��,唐開元間已有詞調(diào)�����。然今傳篇章是否果出于太白,甚難斷定��。今仍錄《菩薩蠻》、《憶秦娥》各一首�。
菩薩蠻
平林漠漠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②���。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③���。玉階空佇立④��,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⑤�,長亭更短亭⑥�。
【注釋】
①漠有廣闊義����?��!澳?�,平遠貌�。②這和杜甫《滕王亭子》:“清江錦石傷心麗”�����,句法極類似��。傷心是重筆�����?�!皞柠悺睒O言文石五色的華美�����;“傷心碧”極言晚山之青�,有如碧玉。③“人”指思念征夫的女子����。孟浩然《秋登南山寄張五》:“愁因薄暮起”����,又皇甫冉《歸渡洛水》:“暝色赴春愁”��,都和這詞句意境相近。孟浩然和李白同時���,皇甫冉比太白年代更后�,李白恐不會襲用他們的句子�。前人詩詞每有一種常用的言語,亦可偶合��。如梁費昶《長門怨》:“向夕千愁起”���,早在唐人之先。意境亦大略相同����。④過片另起�,和上片“有人樓上愁”,不必沖突����。如《西洲曲》:“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這是在樓下�;下文換韻接“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便在樓上了。這些都多方表示盼望之情����?!恫萏迷娪唷贰坝耠A”作“欄干”�。⑤許昂霄《詞綜偶評》:“遠客思歸口氣,或注作‘閨情’,恐誤�。又按李益《鷓鴣詞》云:‘處處湘云合����,郎從何處歸��。’此詞末二句�����,似亦可如此解����,故舊人以為閨思耳�?����!痹S亦無定見���,兩說并存��。但釋為閨情當(dāng)比較合適��。如許說:“樓上凝愁,階前佇立�����,皆屬遙想之詞”,豈非全篇都是想象了��。⑥《釋名》卷五:“亭�����,停也,人所停集也�?��!敝复蟮郎闲腥诵菹⑼A舻牡胤?��。庾信《哀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薄栋资狭肪砣梆^驛門”引庾賦����,并云:“言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p>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①。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②傷別�����。樂游原③上清秋節(jié)�����,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fēng)殘照����,漢家陵闕④�。
【注釋】
①《列仙傳》上:“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shù)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凰飛去�����?��!薄岸稹?���,美人通稱,秦娥猶言秦女,指弄玉��。樓��、臺亦通稱���,秦樓即秦臺。②“灞陵”�����,漢文帝陵����,在長安東,附近有灞橋����,唐人折柳送別的所在�。③樂游苑在漢長安東南,至唐稱樂游原��,一名樂游園�,在長安城內(nèi)升道坊龍華寺之南。曲江在同地�����。④漢代宮殿唐時尚有存者����,如史載貞觀七年太宗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見《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唐紀》)�����。又借漢喻唐,唐人詩中常見�。篇中所云����,不必泥于漢家�����,蓋中晚唐時人傷亂之作�。
韓 翃
韓翃����,字君平���,南陽(今屬河南)人���。天寶十三載(754)進士����。姬人柳氏����,曾為番將沙吒利所奪��,后仍歸韓����。德宗時為中書舍人��。
章臺柳①
章臺柳②,章臺柳�,往日依依③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yīng)攀折他人手��。
【注釋】
①韓翃和柳氏贈答故事���,詳見許堯佐《章臺柳傳》(《太平廣記》卷四八五)�����、孟棨《本事詩》���。②“章臺”,漢長安中街名��,見《漢書·張敞傳》,是繁華的地方�,后來每借稱妓院所在����。六朝、唐人已用其事與楊柳相連�。如費昶《和蕭記室春旦有所思》:“楊柳何時歸��,裊裊復(fù)依依。已映章臺陌����,復(fù)掃長門扉?���!贝迖o《少年行》:“章臺折楊柳�。”《古今詩話》:“漢張敞為京兆尹����,走馬章臺街。街有柳���,終唐世曰章臺柳。故杜詩云:京兆空柳色����?�!保ā豆沤駡D書集成·草木典》卷二六七柳部引���。《事文類聚》后集卷二十三所引略同����,有脫文���,引杜詩“柳色”作“柳市”��,出杜集別本。杜句在《八哀篇·嚴武》詩中��。《古今詩話》已逸�,疑即宋李頎《古今詩話錄》,見《宋史·藝文志》)��。③“依依”����,柔軟貌?!对姟ば⊙拧げ赊薄罚骸拔粑彝?��,楊柳依依�����?�!薄巴找酪馈睆摹度圃姟繁?����,《章臺柳傳》引作“顏色青青”,《本事詩》引作“往日青青”����。
柳 氏
事跡見前�。
楊柳枝
楊柳枝�,芳菲節(jié),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fēng)忽報秋①�,縱使君來豈堪折�。
【注釋】
①《淮南子·說山訓(xùn)》:“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p>
張志和
張志和�����,本名龜齡,字子同,金華(今屬浙江)人����。唐肅宗時待詔翰林���。后隱居江湖間���,自號煙波釣徒。著書名《玄真子》���,亦以自號。
漁 父
西塞山①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②肥�����。青篛笠③�,綠蓑衣��,斜風(fēng)細雨不須歸���。
【注釋】
①《歷代詩余》卷一百十一引《樂府記聞》稱張志和“往來苕霅間作《漁歌子》詞”���。西塞山在浙江湖州市吳興區(qū)西�����。②“鱖魚”,一種大口細鱗,淡黃帶褐色的魚,今呼桂魚���,即鱖之音轉(zhuǎn)�����。③“篛笠”��,篛通作“箬”,竹箬做的斗笠�����。
韋應(yīng)物
韋應(yīng)物(737—����?)�����,長安人���。唐玄宗時為三衛(wèi)郎���。建中二年(781)為比部員外郎�����,出為滁州、江州刺史�����。貞元初(785左右)為蘇州刺史�,后世稱為“韋蘇州”����。所作詞僅存《三臺》、《轉(zhuǎn)應(yīng)》數(shù)曲。
調(diào)笑令①
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②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
【注釋】
①本調(diào)“仄、平��、仄”,凡三換韻。②即焉支山���,在甘肅山丹縣東��?��!妒酚浰麟[·匈奴傳》:“匈奴失焉支山���,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薄把芍А蓖ㄗ鳌把嘀А?���、“胭脂”�����,本植物名���,亦叫紅藍���,花汁可做成紅的顏料�。
劉禹錫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洛陽(今屬河南)人��。貞元九年(793)登進士第,后因王叔文事貶為朗州(今屬湖南)司馬。元和十年(815)召還�,又貶連州刺史�����。晚為太子賓客,加檢校禮部尚書��。禹錫在朗州,曾仿民歌為新詞����。有《劉賓客集》�。
竹枝四首①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瞿塘②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
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
山上層層桃李花,云間煙火是人家�����。
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③���。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情④���。
【注釋】
①《樂府詩集》卷八十一近代曲辭:“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新辭九章,教里中兒歌之�����,由是盛于貞元����、元和之間�����?��!眲⒂礤a原作有小引�。②“瞿塘”亦作“瞿唐”����,長江三峽之一,在重慶市奉節(jié)縣。有滟滪堆��,在江心。③“畬”����,麻韻�����,shē。杜甫《秋日夔府詠懷》:“燒畬度地偏���?����!卞X謙益箋引舊注:“楚俗燒榛種田曰畬�����。先以刀芟治林木曰研畬。其刀以木為柄���,刃向曲謂之畬刀�?!奔此^“刀耕火種”����。耕種三年�,田地須休息一次��,故用《爾雅》“三歲曰畬”的畬字���。④“情”、“晴”諧音�����。古樂府詩廋詞��,或出謎面���,或出謎底��。一般多用謎面���,如“見蓮不分明”,蓮者��,憐也之類����;亦有出謎底者�,如“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期者�����,碁也��?�;蛞浪伪緞⒓鳌暗朗菬o晴還有晴”���?�!稑犯娂肪戆耸唬骸耙蛔髑纭��!弊鲀伞扒椤闭叱鲋i底也����,作兩“晴”者用謎面也。亦有上“情”下“晴”�����,諧音互見,蘊藉出之者,如清人朱子涵《重刊明鈔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七作“道是無情還有晴”��?���!扒椤薄ⅰ扒纭毙嗡埔敉?���,流傳易誤�����。既各有合于古樂府辭例�����,自不妨并存�。今仍從通行本并作“情”字,而記其異文��,以供參考����。
浪淘沙
日照澄洲江霧開,淘金女伴①滿江隈�。美人首飾王侯印����,盡是沙中浪底來②��。
【注釋】
①許渾《題峽山寺》四首之三:“蠻女半淘金�?���!苯鹩械V金��、沙金諸名稱�����。淘沙金稱為“淘金”或“淘沙”。②蓋言王侯貴婦之金錢富貴���,盡是從勞動男女在沙中浪底之辛勤勞動中得來。本篇在唐人詞中���,思想性殊高。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太原(今屬山西)人����。元和三年(808)拜左拾遺����,后貶江州(今屬江西)司馬,移忠州(今屬重慶市)刺史��。后為杭州刺史��,又為蘇州�、同州(今屬陜西)刺史�,以刑部尚書致仕。晚居洛陽�����,自號醉吟先生�����、香山居士。其詩早年與元稹齊名�����,稱“元白”�;晚年又與劉禹錫齊名,稱“劉白”���。詞不多,但影響后世甚大����。有《白氏長慶集》�����。
竹 枝
瞿塘峽口水煙低,白帝城頭①月向西����。唱得竹枝聲咽處,寒猿闇鳥②一時啼�。
【注釋】
①重慶市奉節(jié)縣白帝山上,西漢末公孫述據(jù)此����,自號白帝��,山�����、城因此得名�。劉備伐東吳敗歸���,就死在白帝城。用地名即景�,亦有懷古意�����。②《水經(jīng)注》卷三十四“江水”:“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凄異��,空谷傳響���,哀轉(zhuǎn)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李白詩《下江陵》“兩岸猿聲啼不住”����,到唐代還是那樣�����?!伴湣?��,同“暗”�����。傳世本《尊前集》�����,如黃蕘圃舊藏明鈔本����,《唐宋名賢百家詞》本,汲古閣本���,俱作“闇”,彊村本作“閑”�����,蓋誤�。殘夜鳥啼,作“闇”自好���。白氏本集亦作“闇”�。
望江南二首
江南好���,風(fēng)景舊曾諳①����。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②����,能不憶江南?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③����,郡亭④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游���?
【注釋】
①“諳”���,熟悉。②藍草���,蓼藍�,可制靛青�。③宋之問《靈隱寺》:“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飄����?�!弊髡哂小读纛}天竺靈隱兩寺》詩:“宿因月桂落”,自注云:“天竺嘗有月中桂子落���。”又《東城桂》詩自注:“舊說杭州天竺寺����,每歲中秋有月桂子墮?���!边@不過是中秋晚上到天竺山中賞月罷了�。④“郡亭”,在杭州�,蓋即虛白亭����。作者有《郡亭》詩:“況有虛白亭,坐見海門山��?�!?/p>
溫庭筠
溫庭筠(812—���?)�,本名岐,字飛卿��,太原祁縣(今屬山西)人��。大中初(850左右)應(yīng)進士��,不第��。黜為方城(今屬河南)尉���,改隋縣(今屬湖北)尉,后為國子助教��。卒于咸通八年(867)以前?!杜f唐書》謂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弦吹之音��,為側(cè)艷之詞”�,詞有《握蘭集》�����、《金荃集》,今不傳。唯《花間集》中尚存其詞六十六首���。詩與李商隱齊名���,稱“溫李”����。
菩薩蠻
小山①重疊金明滅②�����,鬢云欲度③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④����。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⑤。
【注釋】
①近有兩說��,或以為“眉山”,或以為“屏山”�����,許昂霄《詞綜偶評》:“小山,蓋指屏山而言”��,說是�。若“眉山”不得云“重疊”����。②承上屏山�,指初日光輝映著金色畫屏�。或釋為“額黃”�����、“金釵”����,恐未是�����。③《詞綜偶評》:“猶言鬢絲撩亂也?��!薄岸取弊趾酗w動意��。④這里寫“打反鏡”��,措辭簡明�����。⑤“帖”�����,“貼”字通,和下文金鷓鴣的“金”字遙接�����,即貼金,唐代有這種工藝����?���!榜唷?��,短衣。繡羅襦上,用金箔貼成鷓鴣的花紋��。
又①
水精簾里頗黎枕②�����,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③。藕絲秋色淺④。人勝參差翦⑤�����。雙鬢隔香紅⑥��,玉釵頭上風(fēng)⑦����。
第5章 上卷 唐五代詞(2)
【注釋】
①本詞詠立春或人日�。全篇上下兩片大意從隋薛道衡《人日》詩“人歸落雁后�����,思發(fā)在花前”脫化�����。②李白《玉階怨》:“卻下水精簾”��;李商隱《偶題》:“水紋簟上琥珀枕”�,表示光明潔凈的境界和這句相類����。“頗黎”,即玻瓈���、玻璃。③張惠言《詞選》評注:“江上以下���,略敘夢境”,后來說本篇者亦多采用張說。說實了夢境似亦太呆���,不妨看做遠景����,詳見《讀詞偶得》���。④當(dāng)斷句,不與下“人勝參差翦”連���。藕合色近乎白�����,故說“秋色淺”,不當(dāng)是戴在頭上花勝的顏色�。這里藕絲是借代用法,把所指的本名略去����,古詞常見��。如溫庭筠另首《菩薩蠻》的“畫羅金翡翠”,不言帷帳�;李璟《山花子》的“手卷真珠上玉鉤”���,不言簾����。這里所省名詞���,當(dāng)是衣裳。作者另篇《歸國遙》:“舞衣無力風(fēng)斂���,藕絲秋色染”,可知����。李賀《天上謠》:“粉霞紅綬藕絲裙��?!雹荨皠佟?���,花勝���,以人日為之,亦稱“人勝”�����?���!肚G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為人日……翦彩為人�����,或鏤金?����。ú槿艘再N屏風(fēng)�,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遺�����。”花勝男女都可以戴�;有時亦戴小幡�����,合稱幡勝。到宋時這風(fēng)俗猶存����,見《夢粱錄》、《武林舊事》“立春”條����。⑥“香紅”指花��,即以之代花����。著一“隔”字,兩鬢簪花��,光景分明��。⑦幡勝搖曳����,花氣搖蕩,都在春風(fēng)中�。作者《詠春幡》詩:“玉釵風(fēng)不定����,香步獨徘徊”,意境相近����。
又
滿宮明月梨花白,故人萬里關(guān)山隔�。金雁一雙飛①��,淚痕沾繡衣。小園芳草綠����,家住越溪②曲��。楊柳色依依�,燕歸君不歸③�����。
【注釋】
①指衣上的繡紋����。②“越溪”即若耶溪���,北流入鏡湖,在浙江紹興市��,相傳為西施浣紗處。本詞疑亦借用西施事����?�;蛞詾樵奖?yún)墙?jīng)由的越溪�,恐未是。杜荀鶴《春宮怨》:“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币嘀溉粢?。③上片寫宮廷光景����;下片寫若耶溪�����,女子的故鄉(xiāng)。結(jié)句即從故人的懷念中寫��,猶前注所引杜荀鶴詩意?���!熬鄙w指宮女��,從對面看來���,用字甚新�����。柳色如舊����,而人遠天涯,活用經(jīng)典語�����。見前韓翃《章臺柳》注③。
又
夜來皓月才當(dāng)午�,重簾悄悄無人語����,深處麝煙長①����,臥時留薄妝。當(dāng)年還自惜��,往事那堪憶?���;湓旅鳉垻?��,錦衾知曉寒③���。
【注釋】
①“深處”承上“重簾”來���,指簾帷的深處?�!镑隉煛?,一作“麝煤”��,都指燭花�。其指香墨時另是一義。以香料和油脂制燭���,叫“香燭”��。作者另篇《菩薩蠻》:“香燭銷成淚�����?��!薄镑隉煛薄ⅰ镑昝骸笔橇硪环N說法��。薛昭蘊《浣溪沙》“麝煙蘭焰簇花鈿”,可互證��。②這里不必紀實�,猶李存勖《憶仙姿》(《如夢令》):“殘月落花煙重�?!被蛐!盎洹弊鳌盎丁?��,恐非。③張惠言《詞選》評:“此自臥時至?xí)?���,所謂‘相憶夢難成’也���?����!?/p>
更漏子
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塞雁�,起城烏①����,畫屏金鷓鴣②�����。香霧薄,透簾幕�����,惆悵謝家池閣③�。紅燭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
【注釋】
①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zhuǎn)》:“城烏初起堞�?!雹凇叭恪?��、“城烏”是真的鳥�����,屏上的“金鷓鴣”卻是畫的��,意想極妙���。張惠言《詞選》評:“三句言歡戚不同���?����!标愅㈧獭栋子挲S詞話》卷一:“此言苦者自苦,樂者自樂”,即張氏說���。李賀《屏風(fēng)曲》:“月風(fēng)吹露屏外寒����,城上烏啼楚女眠��?���!痹~意如本此�����,畫屏中人�,亦未必樂也�����。③“謝家池閣”,字面似從謝靈運《登池上樓》詩來����,詞意蓋為“謝娘家”,指女子所居����。韋莊《浣溪沙》:“小樓高閣謝娘家”���,這里不過省去一“娘”字而已����。
又
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云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①��,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②����,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注釋】
①“梧桐樹”以下,譚獻評《詞辨》:“似直下語��,正從‘夜長’逗出。亦書家無垂不縮之法?���!弊T評末句不大明白����。后半首寫得很直,而一夜無眠卻終未說破�����,依然含蓄���,譚意或者如此罷��。②“不道”�,不理會�����。言風(fēng)雨不管人心里的痛苦。
楊柳枝
織錦機邊①鶯語頻����,停梭垂淚憶征人�����。塞門三月猶蕭索�,縱有垂楊未覺春②。
【注釋】
①借用前秦竇滔妻蘇蕙故事���。蘇氏織錦為回文旋圖詩以贈滔��,事見《晉書·列女傳》��。②“塞門”兩句,翻用王之渙《涼州詞》“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fēng)不度玉門關(guān)”意��,更深一層。張敬忠《邊詞》:“二月垂楊未掛絲����?�!?/p>
南歌子①
手里金鸚鵡,胸前繡鳳凰②����。偷眼暗形相③��,不如從嫁與④,作鴛鴦����。
【注釋】
①譚獻評《詞辨》:“盡頭語�,單調(diào)中重筆����,五代后絕響���。”②這兩句���,一指小針線,一指大針線���。小件拿在手里,所以說“手里金鸚鵡”���。大件繃在架子上���,俗稱“繃子”�,古言“繡床”��,人坐在前���,約齊胸,所以說“胸前繡鳳凰”�����。和下面“作鴛鴦”對照�,結(jié)出本意。③“形相”�����,猶說打量���,相看����。曹唐《小游仙詩》:“心知不敢一形相���?����!雹堋皬摹?���,任從�?��!皬募夼c”,就這樣嫁給他�,不仔細考慮��。
望江南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①��。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②水悠悠③��,腸斷白洲④����。
【注釋】
①《西洲曲》:“望郎上青樓。”②“脈脈”��,含情相視貌�。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弊之?dāng)作“眽”,相視也���。③與《西洲曲》“樓高望不見���,盡日闌干頭”意境相同;詩簡遠���,詞婉轉(zhuǎn)�,風(fēng)格不同。④花白色�����,故稱“白”����。洲�����,水中可住的小島���。《白香山詩集》補遺卷上《送劉郎中赴任蘇州》����,汪立名注引《太平寰宇記》:“白洲在湖州霅溪之東南��,去洲一里。洲上有魯公顏真卿芳菲亭��,內(nèi)有梁太守柳惲詩《江南曲》云:‘汀洲采白,日暮江南春’�,因以為名?���!庇职拙右住兜脳詈輹吩姡骸鞍字奚洗簜髡Z”;后集卷十五附白氏所作《白洲五亭記》說得很詳細�����。這里若指地名���,過于落實���,似泛說較好。中唐趙微明《思歸》詩中間兩聯(lián)云:“猶疑望可見�����,日日上高樓。惟見分手處��,白滿芳洲��?����!焙嫌诒驹~全章之意����,當(dāng)有些淵源。
韓 偓
韓偓�����,字致堯,一作致光�,京兆萬年(今屬陜西)人��。龍紀元年(889)進士���。唐昭宗時以反對朱溫貶濮州(今屬山東)司馬。唐亡�,依王審知。自號玉山樵人����。有艷體詩《香奩集》��。
生查子
侍女動妝奩�,故故驚人睡①���,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淚�。懶卸鳳凰釵�,羞入鴛鴦被②�����。時復(fù)見殘燈,和煙墜金穗③��。
【注釋】
①“故故”�����,故意�。以為人睡著了,久待不耐�����,有意驚醒她。②《古詩十九首》:“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雹蹆删鋵懢蛯嫼笠琅f不眠��。金穗���,燈芯結(jié)為燈花。結(jié)得過長了��,有時會掉下一些火星,寫殘夜光景����。
皇甫松
皇甫松��,名一作嵩,字子奇���,睦州(今屬浙江)人�����。皇甫湜子�?���!痘ㄩg集》稱其為“皇甫先輩”(唐人呼進士為“先輩”,見《資治通鑒》卷二六七)����。
浪淘沙
灘頭細草接疏林,浪惡罾船①半欲沉�。宿鷺眠鷗飛舊浦②�����,去年沙嘴是江心③。
【注釋】
①“罾船”��,扳罾的船�����?���!稘h書·陳勝傳》顏師古注:“罾���,魚網(wǎng)也,形如仰傘蓋��,四維而舉之,音曾���。”②“浦”�����,大水有小口別通�����,亦可作水邊解���。參看下孫光憲《菩薩蠻》注⑨�����。③現(xiàn)在的沙嘴(沙灘)當(dāng)去年還在江心�����,言江沙淤積得很快�。湯顯祖評《花間集》:“桑田滄海,一語道破����?���!?/p>
望江南
蘭燼①落�,屏上暗紅蕉②��。閑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蕭蕭③�,人語驛邊橋④�。
【注釋】
①燈燭之芯結(jié)花如蘭���。李賀《惱公》:“蠟淚垂蘭燼?���!蓖蹒ⅲ骸疤m燼�,謂燭之余燼狀似蘭心也�。”②《格致鏡原》卷六八引《益部方物略記》:“紅蕉于芭蕉蓋自一種���,葉小�,其花鮮明可喜(即今之美人蕉)��,蜀人語染深紅者謂之蕉紅����?���!边@里“紅蕉”����,蓋亦指顏色�����,猶言蕉紅。殘夜燈昏���,映著畫屏作深紅色��。③白居易《寄殷協(xié)律》詩自注:“江南《吳二娘曲》云:‘暮雨蕭蕭郎不歸?�!薄对姟む嶏L(fēng)·風(fēng)雨》:“風(fēng)雨瀟瀟���?��!薄盀t瀟”�����、“蕭蕭”字通,雨下得很急�����。④騎馬以傳遞公文叫“驛傳”�,沿途供他們休息的所在叫“驛舍”�����,或臨水有橋叫“驛橋”�。
又
樓上寢�����,殘月下簾旌①。夢見秣陵②惆悵事③,桃花柳絮滿江城�,雙髻坐吹笙��。
【注釋】
①“簾旌”��,簾額����,即簾子上部所綴軟簾��。白居易《舊房》:“床帷半故簾旌斷��。”李商隱《正月崇讓宅》:“蝙拂簾旌終展轉(zhuǎn)?!雹凇帮髁辍保唇鹆?���,今南京市。③下邊所寫夢境本是美滿的�����,醒后因舊歡不能再遇��,就變?yōu)殂皭澚恕S谩般皭澥隆币徽Z點明夢境��,又可包括其他情事����,明了而又含蓄����。
采蓮子
菡萏香連十頃陂①舉棹②�����,小姑貪戲采蓮遲年少。晚來弄水船頭濕舉棹��,更脫紅裙裹鴨兒年少��。
【注釋】
①《爾雅·釋草》:“荷��,芙蕖……其華菡萏�����?�!薄对姟り愶L(fēng)·澤陂》:“彼澤之陂,有蒲菡萏�?����!壁?����,水邊堤岸��。分言之,荷花含苞的叫菡萏,盛開的叫芙蕖��,但通言沒有分別。②“舉棹”�、“年少”����,葉韻,都是《采蓮子》例有的“和聲”�����。
又
船動湖光滟滟①秋舉棹,貪看年少信船流②年少�����。無端隔水拋蓮子舉棹,遙被人知半日羞③年少�����。
【注釋】
①“滟滟”����,光動搖貌�����。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滟滟隨波千萬里�����。”②“信船流”�,猶“任船流”�����。女子忘卻劃船�����,任它自流�����。③“半日羞”��,羞了好一會兒。倒裝句法�。
韋 莊
韋莊(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屬陜西)人。廣明元年(880)黃巢破長安����,莊在都中,有《秦婦吟》記其事�����。唐昭宗乾寧元年(894)成進士���。蜀王建稱帝��,莊為宰相�。在成都時曾居杜甫草堂故址,故詩集號《浣花集》�����。
浣溪沙
惆悵夢余山月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