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為魂��,以書為骨”,是范曾一生繪畫的顯著特色��。深厚的家族底蘊����,讓范曾長期沉浸于詩文��。從中�,他蘊養(yǎng)了一份涵養(yǎng)深厚的詩魂�,又氤氳到了筆墨深處����,留下了“一紙千金”的盛名���。范曾始終堅信,唯有經(jīng)年累月的辛勞�,才能成為一代大師大家����。他也一直確信�����,“
“以詩為魂��,以書為骨”�,是范曾一生繪畫的顯著特色��。
深厚的家族底蘊��,讓范曾長期沉浸于詩文�。
從中,他蘊養(yǎng)了一份涵養(yǎng)深厚的詩魂����,又氤氳到了筆墨深處,留下了“一紙千金”的盛名����。
范曾始終堅信���,唯有經(jīng)年累月的辛勞����,才能成為一代大師大家。
他也一直確信��,“你越想金錢����,金錢離你越遠(yuǎn)”�����。
因此��,在眾多畫家茫然無解之時��,范曾已經(jīng)找到了他的出路。
“回歸古典,回歸自然”,是他為自己尋找的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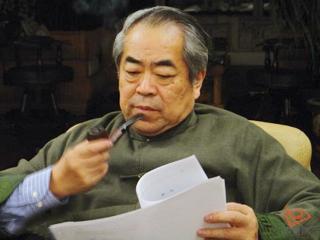
卻怎料,后來是他最早脫離了正軌�����,步入了爭論的漩渦��。
“流水線作畫”��,讓他的事業(yè)接連滾下了幾層階梯。
在作品慘遭市場淘汰之后���,他唯一能做的是��,就是找回自己原本的路�,曾幾何時一紙千金的盛狀���,是否迷亂了他的眼睛��?
范曾的成長路
“我認(rèn)識范曾有一個三部曲����。第一步認(rèn)為他只是一個畫家�����,第二步認(rèn)為他是一個國畫家,第三步認(rèn)為他是一個思想家����。在這三方面��,他都有精湛深邃的造詣”。
東方學(xué)大師季羨林如是說。
范曾出生于延綿450年不斷的詩人世家,這一身份讓他實現(xiàn)了“談笑有鴻儒,往來五百丁”的社交�����。
而他面前��,也自此鋪開了一條更為順?biāo)斓乃囆g(shù)之路。
范曾出生那年,是1938年。
歷史長河正流淌在這個艱難的歲月,全面抗戰(zhàn)的號角也讓國人萌生了再戰(zhàn)的勇氣。
而范曾的家人也沒有斷絕讓這個新生的幼兒走上學(xué)習(xí)之路的想法。
4歲時,范曾開啟了他的求學(xué)之路����。
此后更是一路高歌猛進(jìn)�,屢獲學(xué)校嘉獎�����。
在其他同齡人還為學(xué)業(yè)和未來迷茫之時�����,13歲的范曾已經(jīng)取得了他人生的第一個大的成就。
“南通三小畫家之一”的稱號,給予了年幼的范曾繼續(xù)埋頭努力的勇氣����。
1955年秋天����,17歲的范曾從家鄉(xiāng)南通負(fù)笈北上,來到位于天津的南開大學(xué)求學(xué)��。
自此,經(jīng)由范曾,“南通”與“南開”實現(xiàn)了神奇的連接。
哪怕兩年后,范曾就闊別了南開大學(xué)����,轉(zhuǎn)入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學(xué)習(xí),也沒有影響他對南開和母校師生的關(guān)懷��。
他與南開的情誼,始于1955年�����,往后再沒有斷絕的時候�����。
他想���,南開已是他人生中不能割舍的存在���。他的所有榮譽,都將有南開的一部分��。
而后來他也的確做到了。
1980年后,已然名滿天下的范曾接受了母校南開大學(xué)的邀請,回到了這個他闊別已久的家園。
他一頭扎進(jìn)了籌建東方藝術(shù)系���、培養(yǎng)藝術(shù)人才和成立學(xué)術(shù)基金的工作中。
范曾的成名路
“癡于繪畫�����,能書�。偶為辭章�,頗抒己懷�。好讀書史���,略通古今之變���?����!?/strong>
這是范曾對自己的二十四字自評����。
自明清以來,中國人物畫多以工筆為主�����。
而范曾卻反其道而行�����,學(xué)習(xí)了南宋梁楷以來的簡筆潑墨的手法�。
難得的是��,在這基礎(chǔ)上,他有了自己獨特的風(fēng)格��。
范曾畫人物,可謂傳神。
這固然是名師教導(dǎo)的成果��,卻也有他才思敏捷的緣故���。
范曾在學(xué)習(xí)中國畫之后��,始終認(rèn)為��,中國先哲的深邃感悟����,史家的浩瀚文思��,以及詩家的逸邁篇章�,都是中國畫的源頭活水�����。
因此,他作畫之時�,始終有意地融匯古老中國的“詩�、書�����、畫”,讓它們在靈動的情采中呈現(xiàn)出凜然的風(fēng)骨�。
這些逐漸成為了他畫作的特色。
而筆墨能得范曾的神韻��,也是出于他鍥而不舍的勤奮和努力����。
他未曾改變過去潛心讀書的習(xí)性�,仍舊將大量的時間�����,都用在流連萬卷書香。
他也筆耕不輟,用經(jīng)年累月的辛勞�,實現(xiàn)對心中所思所悟的描繪�����。
他承認(rèn)�����,“人一俗����,人格不高�,下筆必俗�,這是沒有任何方式可以掩蓋的”�。
他也說�,“如果一個人畫畫,每天想著怎么到拍賣場去�����,怎么把自己的話賣得高一些��,越想這個�����,金錢就離你越遠(yuǎn)”。
所以他在自己的書房里���,放上了將近8萬卷的書�����。
哪怕從其中挑出必看的百分之一,都足夠讓他看上30年的時間�。
他要從中去對歷史���、文化�,對世界、東方有一個清楚的了解����,以擺脫低級手藝人的身份����。
他也要再用經(jīng)年累月的辛勞����,去成就自己的大師�、大家之名����。
因此,每天早上5點到7點,范家的書房總能亮起一盞燈,范家的書桌邊,也都或站或坐著一個從年輕到老邁的身影。
這些長期的習(xí)慣�,讓范曾在經(jīng)年累月的積累中,實現(xiàn)了從量變到質(zhì)變的轉(zhuǎn)化。
他逐漸擁有了很多的成就���。
“當(dāng)代畫家中文化底蘊和學(xué)問最好的一位畫家”��、“當(dāng)代擁有崇拜者最多的畫家”�����、“目前書畫界中字畫價格最高的畫家之一”����、“當(dāng)代畫家中納稅最多的畫家”等等,都讓他的聲名越發(fā)響徹國畫界�。
越來越多人以擁有他的字畫為傲��。
范曾甚至曾以414萬元�、782萬元不等的天價,拍賣出了一幅又一幅作品。
范曾的崎嶇路
但就如光明之下必有陰影一般�����。
范曾在享有盛名的同時�����,也必定會遭遇他人的挑戰(zhàn)。
2010年5月,上海《文匯報》發(fā)表了一篇名為《藝術(shù)家還是要憑作品說話》的文章,對國內(nèi)某些不講求藝術(shù)品質(zhì)、大量復(fù)制自己作品�����,進(jìn)行“流水線作業(yè)”的畫家進(jìn)行了批評�����。
雖通篇未點名道姓�,但在看清作者署名為“郭慶祥”之后����,任誰看來���,這篇文章的筆鋒都直指向了范曾�。
范曾與郭慶祥的矛盾由來����,最早要追溯到他們在1995年的一次書畫交易。
當(dāng)時范曾有意在法國購置一處房產(chǎn)���,卻因囊中羞澀而中斷計劃。
無奈之下,他請來有過多年合作的榮寶齋業(yè)務(wù)經(jīng)理米景陽,請他幫忙自己找一個合適的書畫買家���。
米景陽找到了當(dāng)時頗為出名的收藏大鱷郭慶祥���,為范曾成交了一筆涵蓋200幅中國畫�����、100幅書法的大額訂單,并約定價格為1000元一幅��。
在事情定下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郭慶祥就收到了范曾送來的100幅作品。
這讓他在驚訝之余,決心要到現(xiàn)場觀摩�����。
郭慶祥走進(jìn)范曾畫室,第一眼就望向了遍布宣紙的畫墻�。
3平方尺的宣紙�����,一張張地被用吸鐵石整齊地吸附在畫墻上���。
宣紙上畫著的基本都是由幾個人物造型來回組合的相近題材。
這讓郭慶祥在心有所感的同時�,也產(chǎn)生了不滿�。
他想,作品題材重復(fù)過多��,一定會影響他后來的轉(zhuǎn)售��,不利于他的營銷�����。
因此他在期間幾次提出更換部分畫作��,卻還是換來了題材相似的作品����。
直到1997年榮寶齋在大連舉行了一次拍賣活動���,郭慶祥才順勢將買來的范曾作品進(jìn)行了寄賣��。
最終�����,他以數(shù)萬元不等的價格出售完了這一批作品。
盡管從中多有獲益�����,但郭慶祥始終認(rèn)為��,“這種程序化���、模式化的制作過程���,既不是一個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也不如一個美術(shù)工作者的水平?���!?/strong>
因此���,2010年5月,他以一篇文藝批評文章�,隱晦地將范曾送上了《文匯報》的批評榜���。
郭慶祥
郭慶祥在文章中這樣寫道�����,“這位名家其實才能平平”�。
“他的中國畫人物畫��,不過是‘連環(huán)畫的放大’���。他畫來畫去的老子�����、屈原��、謝靈運����、蘇東坡����、鐘馗����、李時珍等幾個古人,都有如復(fù)印式的東西”。
他還寫����,“他的書法是‘有書無法�,不足為式’,裝腔作勢�,頗為俗氣。他的詩不但韻律平仄有毛病����,而且在內(nèi)容上�,不少是為了自我吹噓而故作姿態(tài)��,不足掛齒”���。
對此����,范曾感受到了侮辱和詆毀����。
他很快就以侵害名譽權(quán)的罪名�,將郭慶祥告上了法庭��。
而郭慶祥也在10月之時�����,收到了北京昌平區(qū)人民法院寄來的一紙傳票�。
北京昌平區(qū)人民法院的判決于2011年6月下達(dá)����。
判決中���,郭慶祥敗訴,不僅要向范曾書面道歉�����,還要賠償范曾精神損害撫慰金7萬元�����。
郭慶祥不服判決����,隨后上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但最終,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了原判。
但這次法院也對原告范曾“流水線”作畫事實予以確認(rèn),駁回原告范曾其他訴訟請求。
這樣一來���,郭慶祥雖然敗訴�����,卻站到了輿論的制高點。
范曾盡管勝訴���,且得到了賠償�����,卻也難逃“流水線作畫”的聲討����。
受這一場風(fēng)波影響�,范曾在國畫界的地位和聲望也受到了不小的影響�����。
此后他的新作銷售接連受挫。
范曾隨后在北京榮寶秋和北京匡時推出的14幅作品��,只拍賣出了7幅����,達(dá)到了百分之五十的流拍率,后來他的作品在云南典藏更是敗走市場,一度達(dá)到了百分之百的流拍率����。
這讓無數(shù)關(guān)注后續(xù)的人為之咋舌��。
范曾的攀登路
“流水線作畫”一事爆出��,之所以能給范曾這么大的打擊��,是因為它打擊了創(chuàng)作的獨立性和唯一性���。
一個畫家總是臨摹他人或者重復(fù)自己以往的作品�����,就必定會讓自己的作品失去了應(yīng)有的光彩,淪為復(fù)制粘貼后的“贗品”����。
范曾的行為�����,讓自己一度背離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初衷,淪為了商業(yè)創(chuàng)作的印鈔機器。
也讓他之前的盛名���,出現(xiàn)了不可揮去的污點���。
在早前的一次采訪中����,主持人問范曾,“您是聯(lián)合國特別文化顧問�����,那這個顧問特別在哪兒呢��?”
范曾給的回復(fù)是“特別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少��,少就特別”。
但后來他卻遺忘了這個“物以稀為貴”的道理。
范曾以一場流水線作畫的風(fēng)波,給了自己寶貴的作品一個最沉重的打擊����,也給了日漸浮躁的國畫界一個警醒����。
無數(shù)的藝術(shù)家開始反思自己的舉止,重思過往的初衷���。
但這些來自公眾的輿論��,最終也只讓范曾在原本順?biāo)斓乃囆g(shù)之路上跌了跟頭�。
并沒有剝奪他重新站起前行的權(quán)利��。
2010年��,玉樹地震災(zāi)區(qū)捐款儀式上�,又一次出現(xiàn)了范曾的身影。
范曾為災(zāi)區(qū)的人民捐去的一千萬的善款,加速了災(zāi)區(qū)重建的進(jìn)度����,也加快了災(zāi)區(qū)人民安置的進(jìn)程���。
而往后的歲月����,他也一直延續(xù)著這樣善行。
從1998年到2020年����,范曾一共向國家及政府捐贈了預(yù)估價值多達(dá)60億元的書畫,在多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xiàn)����。
而這種在國家大事��、民族大義面前的慷慨和奉獻(xiàn),也在一定程度上挽救回了他的聲譽。
更多的人逐漸將視線從他原本的污點上挪開����,去關(guān)注他真正的實力和轉(zhuǎn)變。
2013年�,范曾受邀參加了《中國大師路》第二期的采訪,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為主題貫穿了整個采訪過程����。
在采訪的最后,主持人問他����,“范先生���,您目前在做什么�����?”
范曾回�����,“目前我正在舉行一個系列的國學(xué)開講�,大概要講30講�,現(xiàn)在已經(jīng)講了7講”�。
他說,“我要使人知道,國學(xué)不光是儒學(xué)�,更不光是孔子����。國學(xué)里有儒家����、法家����、名家、墨家���、道家��,陰陽家�����、兵家、農(nóng)家����、雜家����、縱橫家����,這個學(xué)問很豐厚����。”
此后,他也以70多歲的高齡,孜孜不倦地向世人宣揚國學(xué),只為增強民族自信心,讓中華文化廣布于天下。
而這也是他對中國文化傳承的掛念和付出�。
與此同時���,他也筆耕不輟,堆起了比他身高還高的著作。
其中出版的著作���,就有畫集、書法集�、詩集����、散文集����、藝術(shù)論��、演講集等一百六十余種。
而在里面的130部均收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供世人學(xué)習(xí)借閱��。
在致力國學(xué)傳承外,范曾在自己的“老本行”——字畫創(chuàng)作中�����,也逐漸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截止到2021年�����,國畫藝術(shù)家范曾已經(jīng)連續(xù)12年登上“胡潤中國藝術(shù)榜”����。
胡潤中國藝術(shù)榜,是前100位中國在世“國寶”藝術(shù)家按照當(dāng)年度公開拍賣市場作品總成交額進(jìn)行排名的榜單。
因此,它向來不會理會爭議,只以作品成交額為唯一考評標(biāo)準(zhǔn)���。
這讓范曾沒有過多受到2010年“流水線作畫”爭議的影響��。
相反�����,借助輿論,范曾在爭論中實現(xiàn)了更高的身價���,獲得了更大的作品成交額����。
范曾第一次登上“胡潤中國藝術(shù)榜”榜首�����,就是在他受到最大抵制的2011年�。
這一年��,盡管他的新作銷售受到了一定的抵制,也沒有影響原本收購他作品的買家實現(xiàn)新一輪的高價轉(zhuǎn)售。
而2012年�����,范曾也以最高的作品成交額�����,再次蟬聯(lián)了“胡潤中國藝術(shù)榜”的榜首之位��。
此后,從2013年到2020年��,范曾在“胡潤中國藝術(shù)榜”的排位時有波動���,卻也基本都穩(wěn)定在榜單前五的名列�。
這無疑是他在國畫界地位和實力的證明����。
可惜的是�,2021年6月“胡潤中國藝術(shù)榜”的發(fā)布����,打破了他以往的記錄。
這位83歲國畫家12年來第一次跌出了榜單前五�����,以1.4億元的成交額排在了“胡潤中國藝術(shù)榜”第6名的位置�。
排在他前面的中國藝術(shù)家有77歲的崔如琢,57歲的曾梵志�����,66歲的周春芽��,57歲的劉野和63歲的張曉剛�。
排在他后面的則是58歲的劉小東,89歲的朱矅奎��,42歲的賈藹力和53歲的毛焰����。
其中����,崔如琢維持與去年一樣的排名���,劉野、范曾下降了一個排名�,其他人均得到了比去年上升的排名���。
但作為唯二以80多歲高齡登上“胡潤中國藝術(shù)榜”且排名在前的藝術(shù)家����,范曾也已取得了很多人望塵莫及的成就。

